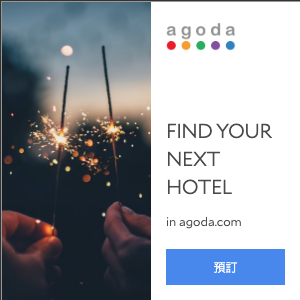貓─村上春樹的分身、替身或化身
 村上春樹先生資料照,取自騰訊大家網
村上春樹先生資料照,取自騰訊大家網
文=李長聲 轉載自《我的日本作家們》一書(東美出版)
與狗狗相比,貓是陰柔的,有點像日本文化。
寫作是孤獨的。有隻貓在書齋相伴,牠就像個擺設,或者讓牠臥在膝頭摩挲,應該不次於辜鴻銘把弄著三寸金蓮淋漓揮毫,難怪日本作家多鍾情於貓。村上春樹特愛貓。大學讀了七年才畢業,在學期間結婚,開爵士樂咖啡館,並開始養貓。他回憶:「我從此把店搬到千馱谷,在那裡寫小說。工作完了之後,夜裡把貓放在膝上一邊慢慢喝啤酒一邊寫第一個小說,那時的事至今還記得很清楚。貓好像我寫小說也不喜歡,經常蹂躪桌上的稿紙。」養狗一般只用來散步,狗跟作家走,或者作家跟狗走,並拾掇狗屎。照片上川端康成兩眼瞪得如貓似虎,看上去很適於養貓,但他的名作《禽獸》裡只寫了養狗,沒有貓。
村上把他與貓的關係寫得很明白,例如:
「想來這十五年間,家裡一隻貓也沒有的時期只有兩個來月。」
「我這八年來居無定所,幾乎是漂泊海外,因而不能悠然靜心養自家的貓。只好時常逗逗近處的貓,聊以滿足對於貓的如饑似渴。」
「兩隻貓也酣然入睡了。看著貓熟睡的姿態,我總會有鬆一口氣的心情,因為相信至少貓安心睡覺的時候並不會發生特別壞的事情吧。」
在處女作《聽風的歌》裡,調酒師傑伊,他是在美軍基地做過工的中國人,講述了一隻被什麼人弄傷了爪子的貓。雖然取名為「鼠」,聽了居然放下啤酒杯,也認為這對誰都沒有好處,不明白為何如此對待並不幹壞事的貓,正如世上毫無理由的惡意多如山。這與他出身於富家卻憎惡富人是一致的。但還有一個自稱「我」的日本人,「『當然不是要殺死,』我撒了謊,『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實驗。』但確實我兩個月裡殺死了三十六隻大大小小的貓。」村上在《海邊的卡夫卡》裡也提及此事。這是貓在村上小說中第一次出現,血淋淋的,或許從村上的經歷我們有理由把這只貓擬村上化。他走紅之後有一個作家撰文,說過去經常和某作家到爵士咖啡館談文學,原來那個在櫃檯裡低頭忙碌的就是他,話裡便含了惡意。
從三島由紀夫給人的印象來說,那麼女氣的人懷裡抱貓最相宜,牽黃擎蒼就有點裝模做樣,更何況切肚皮自裁。他在小說《午後曳航》中凶殘地殺過貓。行刑者「抓住貓脖子提起來,貓沒有出聲,無力地從他手指垂下來。他點檢了自己的心有否產生憐憫,那只是遠遠地一閃而過,於是安下心來」。他一次又一次把小貓摔到木頭上,「覺得自己變成了了不起的男子漢」。作家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磨礪自身的人格,三島其人更這樣。村上小說幾乎離不開貓,他是用那些貓替他說話,甚而有役使過度之感。淡淡的筆調,彷彿帶一點哀愁,或許只有貓的迷離與慵懶才相配,便有了一種日本味。雖然始終有意跟日本文學保持距離,但村上骨子裡終歸是日本的。即便那種為日本讀者所喜聞樂見的翻譯腔,也畢竟是日文的文體,而且很平易,若離開了日文,毛將焉附。
現實中真的有作家殺貓,而且是女作家。事件發生在二〇〇六年,女作家坂東真砂子給報紙寫隨筆,題為《殺貓崽》,說她讓母貓享受了性交與生產的快樂後,把生下來的小貓崽通通丟到崖下去,以免其煩,結果引來了口誅筆伐,乃至有人鼓動焚她的書,不買她的書。聽說她不曾結婚生育,莫非不懂得雌性還具有撫育下一代的本能快樂?她辯解:「我通過貓看自己,愛撫貓是愛撫自己,所以殺剛剛出生的貓崽時我也在殺自己。」那時她住在法屬大溪地島,當地政府要告她,她說這是壓制言論,她是在考慮對於動物來說,何謂生存。好一派作家話語,有如一口井,往下看黑裡咕咚,就叫作深不可測。
村上的貓也下崽,他(牠)們之間的關係已近乎不可思議:「這算是理所當然的吧,貓也有各種各樣的性格,一隻一隻各有想法不同,行動方式不同。現在養的暹羅貓性格非常怪,我不給它握著爪子就不能生。這貓開始陣痛就馬上跳到我膝上,好像喊著號子,用倚靠無腿坐椅似的姿勢坐下不動。我緊緊握住牠的雙爪,小貓就一隻又一隻地生出來。看貓下崽真好玩。」好玩之後,不知他如何處理一隻又一隻的小貓崽。村上去歐洲之前把貓託付給出版社編輯,條件是給他寫一部長篇小說,這就是一九八七年出版的《挪威的森林》,暢銷得如火如荼。
二〇〇二年出版的《海邊的卡夫卡》徹頭徹尾是貓小說,簡直可以叫「圍繞貓的冒險」。中田這個人物會說貓語,為人找貓撈外快,此日正在找一隻花貓(日文寫作三毛貓,可不是《三毛流浪記》畫的三根毛)。「『你好。』這個已步入老年的男人打招呼。貓略微仰起臉,用低低的聲音費勁兒地還禮。是一隻上年紀的大黑貓。」黑貓是可怕的。竹久夢二畫的大美人,懷裡抱一隻黑貓,和她的黑髮形成一體,每見總有點悚然。中田死了,與他結伴旅行的星野「兩點多鐘望窗外,有一隻肥胖的黑貓登上陽臺欄杆,窺視屋內。青年打開窗戶,跟貓搭話打發時間。『喂,老貓,今天天不錯呀。』『可不是嗎,小星野。』貓回話。『我算是服了。』青年說,還搖了搖頭。」人說貓言,貓說人話,在既現實又不現實的世界,村上寫殺貓比三島由紀夫更為慘烈。中田忍無可忍,殺死那個殺貓收集貓靈魂的雕塑家,實際是幫他實現了死亡的願望。為貓而殺人,我們卻這才鬆了一口氣。本來想計算一下村上小說總共寫了多少隻貓,但讀見雕塑家冰箱裡擺放的貓頭,駭得都忘了數數。
貓通常能讓人安然輕鬆,例如《看袋鼠的好日子》寫道:「冬天結束,春天來了。春天一來,我和她和貓都鬆了一口氣。四月裡鐵路罷了幾天工。一有罷工我們可就真幸福。電車一整天連一輛都不在線路上跑。我跟她抱著貓下到線路上曬太陽,簡直靜得像坐在了湖底。我們年輕,剛結婚,陽光是免費的。」
《國境之南 太陽之西》寫道:「我們在我家客廳的沙發上就那麼死死地擁抱。貓趴在沙發對面的椅子上。我們互相擁抱時牠抬眼朝我們瞥了一下,但一聲不吭地伸了個懶腰就又入睡了。」
人之為人,一生下來就要起名,村上在小說中經常給貓起個名字,這是他把貓擬人化的第一步,例如《尋羊冒險記》裡的沙丁魚,《發條鳥年代記》裡的青箭魚,《海邊的卡夫卡》裡的大塚、大河、川村。沙丁魚絕不可愛,「我」要去北海道找羊,走前把這隻貓寄養。司機對我說:「怎麼樣,我隨便給牠起個名可以嗎?」「完全沒問題呀,叫什麼?」「叫沙丁魚怎麼樣?因為以前把牠當沙丁魚一樣對待。」「不壞嘛。」「是吧?」司機很得意。日本人自古瞧不起沙丁魚,把牠寫作「鰯」,武士被罵作沙丁魚是要動刀的。《海邊的卡夫卡》裡咪咪的名字卻是那隻貴婦人似的雌貓自報的,牠對人說:「貓的生涯並非那麼牧歌似的。貓是無力的容易受傷的小生物。既沒有龜那樣的甲殼,又沒有鳥那樣的翅膀。不能像鼴鼠那樣鑽進土裡,也不能像變色龍那樣變色。世上的諸位不曉得有多少貓天天慘遭折磨,白白離開了此世。」這一通貓類自白令人似有所悟,不就是村上最基本的貓觀麼?
走在東京的胡同裡經常有貓出沒,這很像村上的小說。小說主人公常常是「我」,其實那並非村上,貓才是村上本人的分身、替身或化身。貓就是村上,村上就是貓。

《我的日本作家們》(東美出版)
★「文化知日者」李長聲第一本介紹日本作家的主題式隨筆!
★★從明治到平成、從夏目漱石到東野圭吾──37位作家,一部日本近代文學史
★★作家黃麗群、黃崇凱、張維中 一致推薦
★★資深編輯人傅月庵 選編作序
李長聲以隨筆書寫聞名海峽兩岸三地,信筆由之,隨手拈來,日本文化中的食衣住行育樂、風土人情、書店作家……無不躍然紙上,引人會心遐思。本書為李長聲改變寫作風格,由包羅萬象的雜文轉為「主題式隨筆」的第一本著作。此隨筆集以「日本作家」為主題,橫跨明治、大正、昭和與平成4個時代、描繪37位作家,儼然一部日本近代文學史。
※李長聲,1949年生於長春。曾任日本文學雜誌編輯、副主編,1988年起旅居日本,任職出版教育研究所,專攻日本文化史。曾為兩岸三地媒體撰寫專欄,以淺顯風趣的筆調介紹日本文化風情,被譽為「文化知日者」。其隨筆雅俗共賞,創作題材多元,深入淺出描寫日本風土人情及文壇出版等話題,敘事簡練,輕鬆多致,寥寥數筆即得畫龍點睛之妙。已出版繁簡體著作近20種,共百萬餘言,2014年編成《長聲閒話》五冊,總其大成,另譯有《隱劍孤影抄》、《黃昏清兵衛》等。